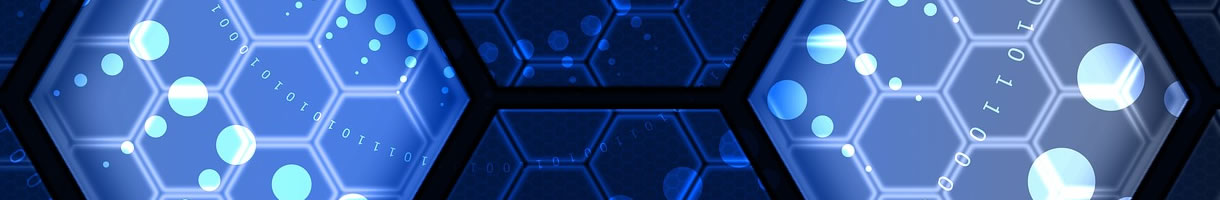繁荣的尽头:一个靠债务续命的世界,终将面临清算!
2025年全球债务池已深达337.7万亿美元,这个看似抽象的数字相当于全球GDP的3倍多,每个地球公民平均背负4.2万美元债务
国际金融协会2025年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债务总额已达到创纪录的337.7万亿美元,仅2025年上半年就增加了21万多亿美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GDP的三倍多,意味着每个地球公民,包括新生儿和老人在内,平均背负着4.2万美元的债务。
当各国政府沉醉于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时,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发出警告,他预测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会出现“债务引发的心脏病”。 债务泡沫的膨胀已接近临界点,而这场全球范围的债务狂欢,终将面对残酷的清算。

一、债务堰塞湖:全球经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球债务规模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从1995年第一季度至2025年第二季度,全球债务总规模增长了437.35%,其中成熟市场国家债务增长295.02%,而新兴市场国家债务更是激增2056.79%。这种增长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堰塞湖。
债务的结构性风险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突出。惠誉警告称,发达市场主权债务水平上升和再融资成本增加,正加剧债务可持续性的挑战。今年,发达市场政府预计将发行约6万亿美元的债券,使其债务总额超过71万亿美元。美国约占发达市场政府债务的一半,更占了2007年起累计增幅的60%以上。

新兴市场的债务偿还压力也在加剧。国际金融协会警告,在2025年剩余时间内,新兴市场将要偿还创纪录的近3.2万亿美元债券和到期贷款。这种偿债压力不仅挤占了发展资源,更使这些国家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异常脆弱。
更令人担忧的是,债务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变化。在低利率时期,政府加杠杆以及政府债务规模的抬升可能并不会引发投资者的广泛担忧,但由于疫情后高通胀的扰动,海外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大幅加息的紧缩政策,利率不断上行无疑放大了财政的脆弱性。

二、债务驱动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债务危机的本质在于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触及天花板。当债务增长持续超越经济增长,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就开始瓦解。
达里奥将美国的财政状况描绘为晚期循环,且危险地自我延续。他引用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数据:每年约1万亿美元的利息支付,约9万亿美元用于债务再融资,以及7万亿美元的支出与5万亿美元的收入之间的显著差距,迫使需要额外的2万亿美元债务。这种不断扩大的供应与投资者对债券作为财富保值工具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的需求下降相冲突。
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困境可作为观察债务危机的微观窗口。2025年上半年,中国上市房企剔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达66.5%,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净负债率大幅上升至171.8%,同比激增55.8个百分点。更值得警惕的是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现金短债比降至0.88,较上年同期再降0.03,意味着超半数房企在手现金已无法覆盖一年内到期债务。

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自1980年以来,对老年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支出在OECD富裕国家中增加了约GDP的5%。老年人拥有政治权力,他们能够抵抗对福利国家结构进行改革,试图保留在寿命较短、生活更艰难时期所制定的福利。
依赖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的空间正在缩小。有分析指出,增加移民只会延迟人口老化的问题,而不会阻止平均年龄上升,最终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相同问题,形成“人口庞氏骗局”。而要弥补美国高达163万亿美元的未來财政缺口,需要7,100万名年轻的高技能移民,这显然不切实际。

三、清算的必然性与可能路径
历史经验表明,所有的债务狂欢终将结束,问题只在于以何种方式结束。达里奥警告,如果一个“政治妥协的美联储”允许通货膨胀失控,可能会出现“当前货币体系的崩溃”。
要使债务累积结束,理论上只有五种选择:大幅削减政府支出、非凡的经济增长、大幅增税、债务违约,或是大规模货币创造(即通膨)。然而,在现实条件下,支出削减和非凡的经济增长被认为不太可能发生,大幅增税面临政治阻力,债务违约对主权国家而言代价高昂,于是通胀成为最可能的结果。
历史上,在二战后(1945年至1980年间),先进经济体有一半时间是透过通膨来冲销债务,使其收益大於支付的利息。在发行本国货币的国家,债權人历史上通常會遭受通膨的损失,而不是违约。

债务危机可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地区爆发。对新兴市场而言,可能是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对发达市场,可能是通胀失控和货币信用受损;对企业部门,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则可能表现为债务违约和资产价格暴跌。
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房企再度迎来偿债高峰期。据克而瑞统计数据,2025年全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高达5257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第三季度单季偿债规模近1600亿元,占比近三成。然而,房企融资难的问题依然突出。2024年,房企债券到期规模4829亿元,发行规模仅2209亿元。这种局面导致房企无法通过借新还旧覆盖到期债务。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全球债务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具体表现。当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债务扩张而非实体价值创造时,整个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便不可避免地加剧。
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层面的掠夺性积累——通过透支未来支撑当下繁荣,但这种透支终将触及自然和社会的极限。当债务增长超越生态承载能力和代际公平的边界时,清算便成为历史必然。
当前的全球债务困境也反映了国家主权与资本逻辑的深层矛盾。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其发行国美联储却只是美国的央行,而非全球的央行。这种矛盾使美元同时承担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品的双重角色,内在冲突难以调和。

黄金作为一种去中心化资产,一定程度解决了全球超级央行缺位的问题。但黄金只能解决资产端全球储备的问题,无法解决负债端的问题,尤其是信用货币时代全球债务不断扩张,以及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向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地再分配。
债务清算的过程将是痛苦而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一场从“资本驱动”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范式革命,将经济重心从债务驱动的虚假繁荣转向人类真实福祉的提升。在这场变革中,那些敢于直面债务泡沫、主动去杠杆的经济体,或许能在未来的秩序重构中占据先机。
当337万亿美元的债务堰塞湖最终决堤,靠债务续命的虚假繁荣必将终结。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被动等待那场毁灭性的洪水,还是主动构筑新的经济现实——一个不再依赖债务膨胀的、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全球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