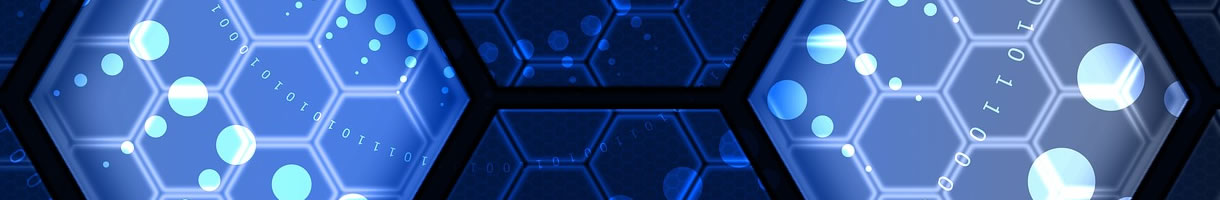中国人在非洲修桥补路建大坝,为什么一直无法取得当地人的好感?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属地化问题,听起来像是一道“送分题”,但实际上却成了长期困扰我们的“课后难题”。明明是自己花了大价钱修桥补路建电站,按道理说,不说当地民心所向,也应该是赢得不少交口称赞,可结果偏偏截然不同。一路走来,我们在非洲的努力似乎总是像脱了靶的箭一般,愿景很美,现实有些扎心。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属地化建设,始终难以真正落地?近些年来,这个问题背后隐藏了许多有意思的细节,也暴露了现实的复杂。

事实上,这一问题并非单纯关乎技巧,而关乎心态、规制和文化形态。举个例子,有位博士出身的中国驻非工程师,在非洲与当地合作方沟通时,用的是全球通用的英语,但整个过程却让人捉襟见肘。他自己语言能力没问题,在国内甚至能流畅地写英语论文,可到了非洲一开会,怎么谈都不对劲,最终不得不依靠会议纪要,来咬文嚼字脑补对方的真实意图。这种头疼甚至成了他的日常,任凭开了数年的会场,依旧学不会怎么与当地人有效沟通。这种语言上的“卡壳”事实上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文化、语境上的隔阂,让一个有语言天赋的博士都被绕晕,何况那些语言基础有限的普通员工。

后来,一个小而务实的调整,彻底改变了他的工作状态——所在的民营企业考察团,专门配了一位当地的中文翻译。这个翻译是马里的本地人,曾经在中国留学,对中非文化了解得颇深,也相当熟悉跨文化的沟通技巧,不仅缩短了语言转换的链条,还打造了某种“信任感桥梁”。奇妙的是,有了这样一个“二传手”之后,沟通效率陡然提高。会后谈判时,他更是意外挖掘到了不少原本目光难以触及的信息,这让他不禁感慨:一个简单的翻译,居然如此厉害,甚至能扭转长期存在的合作难题。而这翻译的费用,仅仅是项目整体成本的九牛一毛,连下午茶的钱都不像。

问题看起来解决得如此轻而易举,但从整个企业运行来企业却鲜有主动去雇用这些当地的翻译。当我们细读其中缘由,会发现,这并不是单纯的不情愿,而是管理者心中早已盘横的种种考量。中非文化差异之大,令许多中国经理难以适应和信任非洲员工,特别是他们那种相对散漫的工作习惯,让很多中方人员觉得非洲工人不敬业、不听话。这些偏见,再加上部分属地员工的确表现欠佳,不免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到一些中方人员宁可咬牙苦学本地语言,也不愿意雇佣属地翻译,直接省略“中间环节”,自以为“牵线搭桥麻烦少”。

另对基层管理者而言,翻译虽然是沟通桥梁,但也可能成为某种“风险”。管理者担忧翻译在话语权上的逐步掌控会变成“权力寻租”的捷径,给企业留下灰色地带,而自己则难以控制。这种不信任的裂痕,让雇翻译和雇属地员工之路越发坎坷。在具体实践中,我们的许多企业干脆采取了“摆烂式应付”:语言没学好,翻译没雇好,就这么拖着,事情大不列颠,草草了结。这个做法,表面看似经济实惠,实际上对企业利益长期损害严重。

仔细剖析,属地化建设的症结背后是一个“文化认知困境”。缺乏属地化管理思维,将非洲视为短期赚快钱的跳板,而不是发展的新土壤,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实际上许多驻非中方人员,常年心态上拒绝与当地社会产生深层次的连接,他们数着在非洲工作的日子,掰着手指头等待返乡。这种“隔岸观火”的工作方式,使得中国企业在当地一直停留在“游牧式”的经营状态,无法扎下持久的根基。

历史证明,无论哪个国家的企业,想要跨国经营并拥有长远发展,都需要完成一件事,那就是属地化。熟悉当地文化,信任属地员工,最终成就一种长期的融合。但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我们面临的环境比欧美国家更复杂:我们的业务高强度又风险高,同时产业链多集中在“苦力型”行业,而非洲本土对这些行业认同感偏低,造成了双向讨厌的局面。

更糟糕的是,企业从高层到基层缺乏系统化的属地思维,甚至连与属地社会日常共存的文化氛围也没有建立起来。相对而言,部分欧洲企业为什么能在非洲相对融洽地运作,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员工更愿意接触非洲文化,甚至培养了发自内心认同当地生活习惯的人。而我们,有时候连吃一顿当地饭都嫌麻烦,这种强烈的排斥与焦虑感,自然挡住了企业文化渗透的脚步。
解决属地化的问题,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务实上,这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企业人的接力;制度上,则需要将推进属地化建设视为一种长远任务,而不是临场抓拍的运动项目。无论是媒体还是企业本身,都需要把快进快退的思维方式转为一种长期主义。正如有学者曾说,“本地化经营从来不是技术活儿,而是文化建设”。属地化建设,不可能速成,但却是迈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有人说,属地化这件事,不在于能否成功,而在于敢不敢开始。如果已有数代一心扑在非洲事务上的中国人,他们的过去,或许正在为中国企业的未来打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