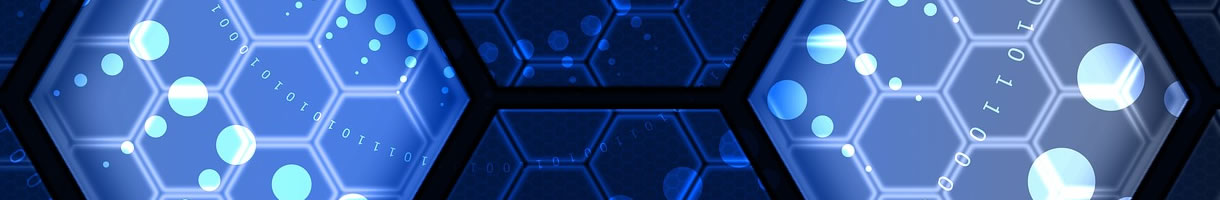周恩来晚年:鞠躬尽瘁的最后十年
身为周恩来同志最年轻的秘书,纪东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诸多重大政治风波,包括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反经验主义等。在此动荡岁月里,他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在重重困难中竭尽全力,奋力支撑国家危局的艰辛与不易。

01
1968年8月12日,对当时年仅24岁的纪东而言,无疑是充满异彩的一天。在这一天,他接到了所在部队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的紧急召唤,被要求至其家中一趟,组织上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待他接手。
纪东接到此通知后,我迅速于下午2点抵达杨德中同志的住处。他随即向我提及此事,表示周恩来同志急需一位年轻的干部担任秘书一职,并征询我是否有意接受此职务。
彼时,我内心洋溢着喜悦,未及深思,便毫不犹豫地应允了我的意愿。他询问我是否有何见解。那时的我,心中唯有喜悦与荣耀之感油然而生,幸福感难以言表。我未曾来得及细述自己的想法,只是坚定地表示愿意,并且郑重承诺定会完成任务。如今回首,当时的回答不过是情感冲动使然,是荣耀感的驱使。至于我是否能够完成任务,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秘书的职责是什么,这些问题我并未深思。
纪东回忆道,那是在1962年,他作为一名新入伍的年轻战士,在北戴河执行值勤任务时,偶然邂逅了周恩来总理。他清晰记得,当时总理正与旁人交谈,言谈间,总理突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如此生动,至今仍历历在目。
纪东8月12日,杨政委与我进行了一次谈话,明确了我在8月15日将正式入驻西花厅办公。到了16日清晨,大约八点钟左右,总理在结束了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之后,径直来到了秘书办公室。
随着距离的缩短,我注意到总理的络腮胡子浓密,头发也已斑白,与六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相比,明显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步伐不再如同往昔那般神采奕奕,显然是一夜未眠的疲惫所致,背部的微倾透露出他的劳累。那时的总理,已显露出深深的疲惫之色。
数月时光匆匆而过,周恩来与纪东的交谈始终未果,直至1969年4月的某个夜晚。
纪东那晚,总理并未外出,而是与邓大姐共进晚餐,两人难得有此相聚时光。餐间,总理将我唤至身边。他言道:“原本打算与你深入探讨,关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掌握秘书工作的要领,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成行。今日,我便以此为契机,正式与你展开交流。你已在工作中分担了一部分任务,表现不俗。未来,希望你能在实践中、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提升。我对你并无其他特别要求,只强调一点,那就是务必注意保密,这是纪律所要求的。”
一是劳累,二是挫败,三是忧虑,四是愤懑。
1970年盛夏的午后,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总理正于休憩之中。纪东步入他的办公室整理文档,偶然瞥见桌上放着一页32开大小的素白纸张,上面总理以铅笔草书了数句戏语:“不公与不干。二月天,最难做人,蚕儿需暖和,参草却盼寒。种菜哥盼雨落,采桑女盼晴朗。”
纪东:因此,我提出总理那首诗或许是在一种无奈心境下所创作的。众所周知,二月和八月是个棘手的时节,人们纷纷胡乱穿衣,时而寒冷,时而炎热,天气变幻莫测,恰逢春夏或秋冬的交替之际。总理通过这几句诗或许是在宣泄内心的痛苦与无奈。然而,抒发完毕后,他依旧需要投身于工作,忘我投入,全盘考虑大局。
当时,总理亲自主持政治局的日常运作。对于一位总理而言,协调各方关系实属不易。在这种情形下,总理的内心有时亦感压抑,这一点我们亦能察觉。总理面露不悦,其神态似乎略显拘谨。
02
1971年9月13日,在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个不寻常的日子。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被党章确认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拖妻带子,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疯狂北逃,后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三事件。纪东回忆说,周恩来从得知这一消息开始,便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查问情况,布置工作,不眠不休,三天三夜。纪东作为总理的秘书,跟着他度过了紧张的几十个小时。
纪东我始知此事,乃是在9月13日清晨,接到广州军区丁盛的电话之时。总理嘱托小纪火速前往人民大会堂,并随身携带电话记录。我携带着这份记录抵达人民大会堂,总理便告知,自此刻起,不得归家,须随其处理事务。
纪东回忆道,9月12日晚,他正于西花厅值勤之际,接到时任海军政委李作鹏的电话,通报256号三叉戟飞机已停靠于山海关机场。翌日凌晨4时有余,总理的另一名秘书钱嘉东将纪东从沉睡中唤醒,告知北京卫戍区传来消息,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地区紧急降落,被民兵所围,并称已向总理汇报。纪东回忆称,当时他们觉得事态颇为异常,却难以揣测背后的原因。直至晨曦初现,7点半左右,他们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电话,要求向总理汇报相关情况。
纪东丁盛的电话中,出现了“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我们就与其斗争到底”的说法,这在以往是未曾听过的。过去,人们会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党中央,我们就与他斗争到底”,而今林副主席已不在,这不禁让我们心生疑问: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们不敢过多议论,也未深思其因,但总理一连多日未归,这样的情况极为罕见,往日不管多晚他总会回家安睡。至于邓大姐那边,情况也不得而知。我们俩开始推测,国内近期是否有异常的动静,是否看到了令人不安的材料,但经过反复思量,我们并未发现任何端倪。然而,我们总觉得似乎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丁盛的电话也显得格外可疑,但我们又不敢过多揣测。
9月13日晨8时,纪东步入人民大会堂,他犹记得周恩来当时神态从容,却难掩疲惫之色。事后纪东方才得知,那时林彪所乘的飞机已从中蒙边界上空神秘失踪,已有超过六个小时。自9月13日拂晓起至午后,周恩来亲自拨通了11个大军区以及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关键负责人电话。
纪东:总理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打电话,通知他们有这么一件事,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作报告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和儿子,逃跑了,是用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一般的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人就会知道是谁,但是在电话中并没有说林彪,有时候电话信号也不好,对方说听不清楚,请总理重复一遍,总理又得重复一遍,我见到总理的时候,他的嗓子都是沙哑的。
此刻,纪东与众多人等共处焦虑的等待之中,直至外交部的一通电话打破了沉寂。
纪东:“你看,你看,果然如此,飞机坠毁了,坠毁了。”他示意我观看,方知那架飞机不幸机毁人亡,坠毁于温都尔汗科特省的温都尔汉矿区,四周尽是草原。飞机在强行着陆时翻转,随后发生爆炸。
纪东回忆说,当时在整个人民大会堂里,只有总理和他两个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周恩来到118房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针对九一三事件和林彪集团的一系列调查随后展开,周恩来被任命为林彪专案组组长。纪东回忆说,在九一三事件后一个来月的一天早上,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的周恩来按响电铃,把他叫进了办公室。
纪东:我提及,总理召唤了我,他应声后便严肃地说要谈一桩事。这种语气,已很久未从总理口中听闻,我心中不由得紧张起来,心想:究竟发生了何等重大的事情?他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1971年10月几日”。我并未感到惊讶,以为总理是笔误,因自九一三事件后,总理给主席的报告屡见不鲜,却从未有过这样的错误。我想,或许是因为他自起床至我接班,未曾合眼,至少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疲劳至极,这才导致这样的笔误。他告诉我,信的内容已经写好,但信封却弄错了,让我撕掉信封,并提醒今后要严格把关。我照做了。当时我心中疑惑,信封撕了不就解决了,为何还要让我进去?然而,总理并没有这么做,他明确表示,这是要告知我们替他把关,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错误。
03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际,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两次向纪东提及,总理在林彪叛逃之后曾对国务院领导表示,中央的问题尚未解决,他的心境颇为沉重,这种难处不仅仅源自林彪事件。总理述说这番话时,眼中闪烁着泪光。纪东对此并未作答,只是淡然一笑。纪登奎感慨地叹了口气,总理承受的压力也不易。至1972年3月5日,江青下令秘书紧急召集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至钓鱼台17号楼“议事”,指责其身边的护士赵柳恩意图对她下毒,从而引发了一场风波。为平息这场争议,周恩来主动提议将自家的护士许奉生调拨给江青。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平时不见踪,偶尔露锋芒。”
纪东依据总理的指示,部长级及以上领导的信件均不得擅自拆封,至于知名人士的来函亦是如此。于是,当收到江青的这封信时,要么在江青面前拆阅,要么由他自己动手。而这封信,我正是在江青的面前拆开的。拆开后并未阅读,便直接呈交给了总理。总理阅毕,不禁说道:“这是一首诗,你来瞧瞧。”我心中暗想,既然总理如此说,那便看一下吧。
我取过纸张,开始在上面挥毫泼墨,书写五言诗,遵循着平仄的规律——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总理亦循着音律作画,然而画至第二句,他却指出这不合平仄,便对我说:
“那还作什么诗呢?拿去吧,自己去修改。”话音刚落,那诗便易主于我。我心想,我还能修改这首诗吗?事实上,我也确实无能为力,因为我之前已被总理评价为五音不全,发音不准。
我向总理坦诚相告,我的发音确实不够准确,尤其是在平仄上,这种发音的纠正并非我能左右。我原本打算放弃,但心中明白总理提出让我修改,实则是对我能力的信任,以及对这首诗的呵护。尽管如此,我还是收下了这首诗,将它放置在我们值班室的角落。总理之后并未再提及此事。按照我们的惯例,一旦总理不再过问,我们便会将相关事宜放入一个固定的文件夹中,无需再行审批。我随时可以取出,若无人询问,便让它静置。那封信便一直如此放置着。至于她那首诗,大约过去了一个月,我在《人民画报》上看到了它的发表,甚至还附有照片,至于其中的其他细节,我就不得而知了。
1972年5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在这一时期收到了成效。在政治上,批林整风运动,解放了大批老干部,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职务。在经济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时间进入1973年,北京的政治空气日渐凝重。到了1973年11月13日,由于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军事问题的会谈。事后,毛泽东大发雷霆。
纪东:此事的起源并不复杂,只是有人向主席反映,称总理在中美谈判中表现出偏颇。主席误信了这一反映,以为总理有所偏向,因而组织了一次对总理的批评。甚至提出,要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学习外语,以防受他人误导。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会者自然要遵循主席的指示,对总理展开批评,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
在严酷的政治氛围中,众多人揣摩领导意图,纷纷与周恩来保持距离,会场因此呈现出对他进行围攻和批斗的一幕。“卖国求荣”、“屈膝投降”、“无视中央”、“欺骗主席”,周恩来一时间陷入困境。江青更是借题发挥,宣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声称周恩来“迫不及待地意图取代毛主席”。
纪东然而,当批评达到一定程度,主席便宣告停止,表示无需再继续。自然,批评便随之止息。总理的一生,对于他人对其错误行为的指责,或是他本人意识到的过错,总理总是勇于检讨,并承担起责任,严于律己,剖析自我。在此次会议上,总理亦秉持这一态度,最终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至于此事,对于那些批评他或曾错误反对他的人,总理历来未曾追究个人责任,也未曾与他们疏远,对他们毫无戒备和怨言。据我印象,我从未听闻总理说过任何人的坏话,确实如此,未曾听闻。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周恩来的政治处境愈发艰难。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1974年春天,由于大量便血,周恩来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
纪东:在这期间,曾有一次我们原本已达成共识,政治局成员对此均有了解。总理下午需要接受输血治疗,王洪文的秘书给我来电,告知江青同志急需确定当晚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以便安排其他活动。我建议是否可以稍作推迟,随即向钱佳铜同志和大姐进行了汇报,并正式回复了王洪文,表示总理正在进行输血,预计半小时后完成,待总理输血结束后再行决定会议时间。
令纪东始料未及的是,仅仅五分钟后,王洪文的秘书便再次来电,强调会议时间需即刻确定。
纪东我亦不敢再施加压力,亦不敢多言,于是与大姐、钱佳铜商议。显然,不报告此事已是不行了,然而如何报告呢?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决定由我撰写一份简报。简报中提及,王洪文同志来电告知,江青同志需确定今晚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以便她能够安排其他活动。据此,我起草了这份简报,并从门缝中悄悄塞入总理的房间。当时,总理的房间里有正在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正在为总理输血。我便请他们适时向总理报告此事。总理的保健医生见到这份简报,亦意识到此事非报告不可,否则纪东不会单独写这张条子,这显然是经过外部商议的结果。于是,他唤醒了总理,告知江青同志需要确定晚上的活动安排。总理听闻此言,顿时怒火中烧,毅然拔下针头,拒绝继续治疗。
04
1975年二月,张春桥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警惕经验主义的潜在危害,并将反对经验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原则。他更进一步,指责周恩来在1972年对极“左”思想的批判是“追随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并暗指周恩来主持的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可能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同年三四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利用他们控制的媒体,接连推出多篇报道和文章,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最主要的危险,从而引发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狂潮。纪东回忆称,当时周恩来总理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是明确且坚定的——坚决对抗。
纪东:总理对于这种经验主义的倾向素来持反对态度,主席亦表示了同样的立场。总理坚持,经验和经验主义实为两回事。即便身患重病,总理仍坚持要求我们搜集张春桥在总政的讲话《宣传批经验主义的问题》,以及各式小报,并找寻相关的电报资料。
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的批示站到了周恩来一边。
纪东“怎能如此对待老同志?他们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工作经验,这岂能被冠以经验主义之名?你把那小报找给我看看。”他当时的话语十分具体,因此,那股批判浪潮最终未能继续,得以平息。
1975年10月下旬,病情严重的周恩来总理已无力离开病榻起身。据相关资料显示,自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总理共经历了14次手术,与各界人士进行了233次交谈,接待外宾63次,主持及参与会议40余场。在这期间,他于医院内召开会议20余次,而外出参会则有20次之多。
纪东:医者、警卫,乃至我们秘书,即便是大姐也不例外,我们无不深切地关注着总理的健康状况。我们曾多次力劝他,应适时休息,稍作休养,即便只是短暂几日的休憩,亦足以缓解工作压力,待恢复后再投身职责。医者们更是频繁从病情角度出发,对他提出警示。然而,总理却告诉我们:“总理啊,我是国家的总理。在这关键时刻,无论谁来顶替,这份工作都非我莫属。”
纪东回忆道,多年置身于总理的身边,他深知总理对京剧的钟爱、对乒乓球的热爱,以及与孩童们相处的喜悦。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时间紧迫,这些往昔的乐趣变得尤为珍贵。对于周恩来而言,睡眠甚至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奢侈。
纪东总理非但非因自然醒而起身,往往是秘书轻唤其梦乡。在睡前,他早已安排妥当,何时何分需被唤醒,皆因外宾将至,会议在即。故而我们呼唤他时,总是精确到秒,不愿让他提前片刻。目睹他沉睡得如此香甜,心中虽有不舍,却不得不忍痛唤醒。因此,他的起床也实属无奈之举。总理曾感慨:“我也想休息,何时方能得闲?”他同样疲惫,同样身为血肉之躯。
纪东犹记,在总理住院期间,他不仅时常通过电话向秘书们布置工作,更有时亲自召集他们,面对面地进行事务交代与文件整理。在这些经历中,最令纪东难以忘怀的,是在最后一次进行文件清理时,周恩来总理从众多文件中精心挑选出了一份。
纪东我指出这份文件所涉内容,关乎铁道部和铁道兵两部,鉴于其中领导同志涉及林彪政变,故曾调动一个营的兵力介入此事。当时,他向我明确表示,调配该营兵力一事并非如此简单,他要求我务必铭记,待他出院后,他将亲自对此事进行处置。我自是牢记于心。然而,遗憾的是,总理未曾得以处理此事,因他此后便再未走出医院,未能重返办公岗位。
在纪东的记忆中,那份文件成为了总理临终前最后需要处理的公函。1975年10月,周恩来同志再度入院治疗,纪东被指派留守西花厅处理日常事务,自此两个月间未曾与周恩来同志谋面。经过屡次恳请,直至1975年12月31日,他方获准探望病情严重的周恩来同志。
纪东:那一次与总理的会面定格在1975年12月31日的正午时分。据医生与他的卫士所述,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意识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得知总理当天希望与我见面,他的警卫便紧急电话通知我即刻前往。我们抵达时,只见病床上的总理已显得异常消瘦。
总理仅轻轻抬了抬右手,以微弱的嗓音向我们说道:“你们来了,代我向家人问好,我有些疲惫了。”短短的这三句话,正是在他逝世前的不足一周,那时他才首次表达出他的疲惫。
目睹他之后,他再度陷入了沉睡。他的卫士向我告知,我们实属有幸,因为在他与你们交谈之际,他尚且保持着清醒。总理自己也感慨,“文化大革命”让我损耗了多少岁月。这竟是我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