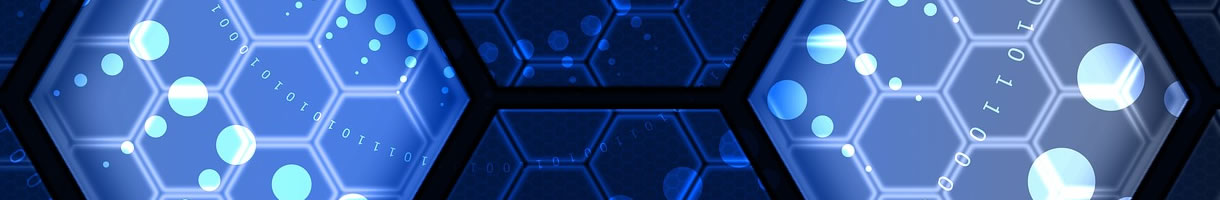青岩军区那年,我放下深爱,戈壁荒漠寻新生
声明:本文故事情节均为虚构,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请勿对号入座。图片仅用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站在青岩军区的操场上,军旗猎猎作响,像在诉说我的心事。
顾景舟,他是我十几年的信仰,也是我最深的伤口。
他爱的是白雪柔,可我却傻傻守着他,以为时间能换来他的心。
昨晚,我烧掉了所有画着他的素描,火光映着我的泪水,我问自己:简月清,你还要不要继续爱一个不爱你的人?

1
操场上的风带着戈壁的沙砾,刮得脸颊生疼。我站在青岩军区大楼前,仰望军旗。广播里,激昂的声音回荡:“科技创新引领,军队改革迈进!”我深吸一口气,默念:“爸,妈,我会继承你们的遗志,扎根西北,报效祖国!”敬礼时,手指微微发抖。
“月清。”顾景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低沉又熟悉。
我转过身,看见他拿着训练报告走来,军装笔挺,眼神却冷得像冬天的戈壁。他问:“你在干什么?”
我笑了笑,掩住心底的酸涩:“向信仰许愿。愿顾团长一生平安,也愿我和喜欢的人永不分离。”
他愣了愣,随即露出浅笑,伸手理了理我的肩章:“都定亲了,还会分开吗?”
我低头,没回答。风吹乱了我的发丝,也吹乱了我的心。定亲三年,他的心却从没属于我。
傍晚,军区大院的灯光昏黄。我和顾景舟各自结束训练,回到宿舍。刚到院门口,警卫员匆匆跑来:“顾团长,白同志又犯病了,医生说需要家属安抚。”
顾景舟脸色一变,转身就走。走了两步,他回头看我,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去吧。”我语气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他点点头:“晚饭等我,我很快就回来。”说完,他大步消失在夜色里。
军嫂们围过来,七嘴八舌:“月清,你可真大度。白雪柔是顾团长的老相好,你就不怕他们旧情复燃?”
“是啊,雪柔父母去世后,顾团长把她接到大院照顾,三年了!你看着他天天关心她,不难受?”
我垂下眼,笑了笑:“没什么好难受的。”话虽如此,心却像被针扎了一下。
回到宿舍,我点燃炭火炉,拿出这些年的素描本。每一页,都是顾景舟的模样。眉眼俊朗,笑容温暖。我轻轻抚摸画纸,思绪飘远。
八岁那年,父母因科研事故牺牲,我被顾母收养。第一次见到顾景舟,他穿着军装,站在院子里,像一棵挺拔的松树。我哭着想爸妈,他把我抱在怀里,轻声说:“别哭,我会永远陪着你。”
永远有多远?我不知道。为了这句承诺,我守着他,从少女到如今。
顾母希望我做她儿媳,定亲那天,顾景舟醉得一塌糊涂,拉着我的手说:“最后还是我们在一起了。”我以为那是爱,后来才明白,他惋惜的是和白雪柔的爱情。
炭火烧得正旺。我一页页撕下素描,扔进火里。火光吞噬他的脸庞,像在烧掉我多年的痴心。
门响了。陈燕走了进来,科研中心的战友,风风火火。她一把抱住我:“月清,听说你申请回科研队了?真的?”
我鼻尖一酸,点点头:“真的。”
她眼眶红了:“你离开后,队里实验都停滞了。我们需要你!”
我低声说:“对不起,让你们等了这么久。”
陈燕咧嘴一笑,伸出手:“没事!我们又能并肩作战了!”我握住她的手,重温誓言:“科技强军,砥砺前行!”
夜深了。顾景舟推门进来,满头大汗:“临时开会,晚了。”他放下铝饭盒:“去国营饭店买了菜,趁热吃。”
我看着饭盒,愣了愣。他夹了块辣烧鱼给我:“你最近瘦了,多吃点。”
我手一顿,低声说:“谢谢。”我从不吃辣,他却忘了。三年同居,他连这点小事都不记得。
饭后,我收拾碗筷,余光瞥见他房间亮着灯。透过门缝,他正笨拙地缝补一件蓝色连衣裙。那是白雪柔的。我心一沉,推门进去,拿过军大衣披在他肩上:“降温了,小心感冒。”
他没抬头,继续穿针引线:“雪柔最喜欢这件裙子,非要我补。”
我轻声说:“从里面缝,针脚就看不见了。”
他一愣,笑了:“你还是比我强。”他顿了顿,语气温柔:“雪柔性子软,可倔得很。因为是我送的,她舍不得扔。”
我没说话,接过裙子,默默缝好。针线穿过布料,像刺穿我的心。
清晨,阳光洒进宿舍。我收拾好行囊,准备去科研所报到。警卫员拎着一堆东西跑来:“嫂子,顾团长一早去供销社买的鸡蛋、水果,还有麦乳精,让你好好休息。”
我看了一眼,平静地说:“收下了,麻烦转送给白雪柔同志。”顿了顿,我补充:“我和顾团长没结婚,以后别叫嫂子。”
警卫员一愣,挠头走了。我背上包,头也不回地离开。
科研所里,同事们忙碌如常。我刚报到,就被安排进西北实验队。陈燕拉住我,欲言又止:“月清,这一去四五年,你和顾团长……”
我打断她:“再说吧。”我已经不想再提他。
回到宿舍,我开始搬花盆。那棵桂花树,是我三年前亲手种的,如今开了花。我让人连根拔起,送给邻居。院子空了,心也空了。
电话响了。是顾母的保姆:“月清,景舟和他娘吵起来了,赶紧回来!”
我一惊,匆匆赶到顾家。门外,顾母怒吼:“你要娶白雪柔?疯了!跟你定亲的是月清!”
顾景舟声音坚定:“妈,我讨厌包办婚姻。当初是你逼我跟月清定亲,我没亏待她。雪柔身体不好,只能靠我。我娶自己喜欢的人,有什么错?”
我攥紧拳头,推门进去。顾母见我,眼中满是心疼:“月清,你听到了?”
我点点头,坐在她身边:“妈,我想让景舟娶雪柔。”
顾母震惊:“你从小喜欢他,熬了这么多年,怎么舍得?”
我眼眶泛红,握住她的手:“妈,景舟对雪柔的感情,就像我对他的,爱而不得最遗憾。所以,成全他们吧。”
顾母叹气,泪水滑落。我强笑:“我做不了您儿媳,但永远是您女儿。”
顾景舟站在门外,皱眉看着我。我走过去,平静地说:“我说服妈了,你可以娶雪柔。”
他愣住:“为什么?”
我笑得释然:“我们是兄妹,也是战友。你想要的,我都支持。”
他突然抱紧我:“谢谢。”他的声音颤抖,像在压抑什么。
我心一痛,明白这拥抱无关爱情,只是感激。
半个月后,顾景舟和白雪柔的婚礼在军区礼堂举行。政委证婚,他俩喝了交杯酒。家属席上,我看着他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心像被刀割。
定亲时,他从未这样笑过。
宾客散去,顾景舟走来,带着酒气:“要不是你,我不知什么时候能跟雪柔在一起。谢谢。”
我擦掉他嘴角的酒渍:“快去吧,别让新娘等久了。”
他摸摸我的头,像小时候那样:“我还是会把你当妹妹疼,永远陪着你。”
我看着他和白雪柔挽手离开,眼泪终于滑落。这是我第一次为他哭,也是最后一次。

2
我站在顾母的客厅里,心像被撕开一道口子。顾景舟的话还在耳边回响:“我讨厌包办婚姻。”他爱白雪柔,爱得那样深,连我多年的付出都成了多余。我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痛得让我清醒。
顾母拉住我的手,眼中满是心疼:“月清,你怎么舍得把景舟推出去?”
我强挤出一丝笑:“妈,爱而不得最遗憾。我不想他遗憾。”
她叹气,泪水滑落:“你这傻丫头。”
我低头,眼眶湿润。顾景舟站在门外,眼神复杂,像在挣扎什么。我没看他,径直走过去:“我说服妈了。你可以娶雪柔。”
他愣住,喉结滚动:“为什么?”
我笑得平静:“你是兄长,也是战友。你想要的,我都支持。”
他突然抱紧我,声音低哑:“谢谢。”那拥抱炙热,却像刀子,割在我心上。
我推开他,抬头望天。星光昏暗,像我对他的心,早已黯淡无光。
半个月后,军区礼堂张灯结彩。顾景舟一身军装,笑容灿烂。白雪柔穿着白色婚纱,柔弱得像一朵风中的雪花。政委举杯:“祝二位百年好合!”
我坐在家属席,端着酒杯,手指冰凉。交杯酒映着灯光,刺痛我的眼。他们笑得那样幸福,而我,像个局外人。
宾客散去,顾景舟走来,带着酒气:“月清,要不是你,我不知什么时候能和雪柔在一起。”
我擦掉他嘴角的酒渍:“快去吧,别让新娘等久了。”
他摸摸我的头,像小时候那样:“我会把你当妹妹疼,永远陪着你。”
我看着他和白雪柔挽手离开,背影那么般配。心明明不痛了,眼泪却止不住。军嫂们说我不争气,可谁知道,成全他,是我给自己最后的救赎。
次日,我收拾行李,准备搬回自己家。院子里的花盆全搬走了,空荡荡的,像我心里的那片荒漠。顾景舟推门进来,皱眉:“院子怎么光秃秃的?想种别的,我让人帮你。”
我摇头:“雪柔身体不好,我们忙,没时间照顾,就送人了。”
他看着我,眼神深沉:“月清,你要搬走?”
我点头:“我家离科研所近,工作方便。”
他皱眉,打断我:“是因为我和雪柔结婚,你觉得不方便吧?我不同意你一个人住。”
我愣住。他的语气里有不舍,像在挽留。我垂眼,低声说:“景舟哥,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新开始。”
他沉默片刻,叹气:“你倔脾气,决定的事不会改。行,我抽空帮你搬。”
两天后,他把我的行李搬上车。白雪柔想帮忙,他却让她回去休息。我站在门口,面向朝阳,深吸一口气。像挣脱了枷锁,轻松,又空落。
顾景舟抱住白雪柔,低声安慰。我释然一笑。他们会幸福,而我,该和过去告别了。
我去了烈士陵园。父母的墓碑冷冰冰的,我放下菊花,眼泪终于落下:“爸,妈,女儿来看你们了。”
我蹲下身,声音哽咽:“妈,你说别把爱情看得太重。可我爱了他那么多年,还是没留住他。”
风吹过,墓碑无声。我擦干泪,站起身:“现在我懂了。比爱情更重要的,是我自己。”
顾景舟走来,给我披上外套:“天冷,加件衣服。”
他转向墓碑:“伯父伯母,我会照顾好月清,绝不让她受委屈。”
我看着他,眼神微动。他总觉得,只要不伤及爱情,其他都不算委屈。可他忘了,我的委屈,从来都因他而起。
夜色浓重,街上热闹起来。顾景舟买了个烤红薯,掰开递给我:“尝尝,你最喜欢的。”
我咬了一口,香甜中带着苦涩。他笑着说:“雪柔也爱吃,但她胃不好,不能像你这样吃。”
我手一顿,低头不语。他连我的口味都不记得,却事事想着白雪柔。这就是不被爱的真相,连一分一毫都不值得他惦念。
他突然问:“月清,你的胸针呢?”
我一愣。那是他送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我从未离身。我低声说:“忘家里了。”
他皱眉,揉揉我的头发:“没事,一会儿带你去买新的。”
我没说话。他走进老凤祥,店员热情介绍:“新品龙凤镯,寓意百年好合。”
顾景舟眼睛一亮:“雪柔会喜欢。”
我心一沉,转身走向电话亭。拨通科研所的号码,陈燕接电话:“月清,出发时间提前了,明天早上走。”
我坚定回答:“我和你们一起走。”
挂断电话,我回到家。屋里积了厚厚的灰,我打扫干净,累得满头大汗。门响了,顾景舟冲进来,气喘吁吁:“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急死我了!”
我递给他一杯茶:“你忙着,我没想打扰。”
他握住我的手,声音沉哑:“以后别这样了。”
我抽出手,平静地说:“我收拾好了。你回去吧,雪柔需要你。”
他皱眉,把饭菜往桌上一放:“听说这附近治安不好。我明天送你去科研所。”
吃饭时,他突然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你躲在房间哭,叫着爸妈。我嫌你爱哭,可你叫我‘景舟哥’,我就想永远护着你。”
我手一顿,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他继续说:“这些年,你为我做的,我都知道。”
我放下筷子,垂眼不语。他以为那是深情,可我只觉得讽刺。他爱的始终是白雪柔。
夜深了,我推开他房间的门。他睡得沉稳,眉眼依旧俊朗。我伸出手,隔空描摹他的脸。这张脸,刻在我心上,可我还有几十年,够我忘记。
“明月……”他梦呓般叫我的名字。
我手一僵,心酸得像被碾碎。这是他第一次在梦里叫我,却也是最后一次。
天亮了,我背上行军囊,走出房间。楼下,收音机传来歌声:“路漫漫,雾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
我朝军区方向敬礼:“再见了。”步履坚定,我走向火车站,没再回头。
3
火车轰隆作响,窗外戈壁荒漠一望无际。我坐在卧铺上,手里捏着科研资料,心却空荡荡的。顾景舟的笑脸还在脑海,可我告诉自己:简月清,你该放下了。
车厢里人声嘈杂,饭菜味混着汗味。我低头看资料,试图让自己专注。忽然,一双军靴停在我面前。我心一跳,抬头看去。
“同志,箱子能挪一下吗?”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我连忙道歉,把箱子挪到一边。来人穿着常服,背着作战包,腰窄肩宽,标准的军人身形。他低头整理行李,短发下透着股慵懒的硬朗。
我偷瞄一眼,心莫名一颤。他的眼神扫过来,冷峻得像刀锋。我赶紧低下头,脸颊发烫。
中午,火车停靠站台。小贩叫卖盒饭,香气飘进车厢。我正要招手,汽笛响起,小贩一哄而散。我叹气,坐回原位。资料不能离身,我只能等餐车。
对面的人递来一份盒饭:“吃吧,刚才看你没买到。”
我愣住,抬头看他。他眼神平静,却带着审视。我犹豫片刻,接过饭盒:“谢谢。”
他没说话,转身坐下。我小口吃着,饭菜味道一般,却莫名安心。吃完,我估摸着饭钱,悄悄放在他枕边。
他回来时,瞥了眼钱,没吭声,收了起来。我们像达成了某种默契。
几天下来,他每天帮我买饭,我吃完放钱。车厢晃荡,阳光洒进来,暖得像久违的拥抱。我靠着窗,望着雪地融化的痕迹,心底生出一丝希望。
这天,饭点到了,他却没回来。我有些不安,攥紧资料。周围乘客吃完饭,香气散去,他还是没出现。我拉住乘务员:“对面那位先生,可能没赶上车?”
乘务员皱眉:“你们认识?如果他没上车,行李得寄存。”
我沉默了。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怎么确认?我摇头:“不确定,您先忙。”
夜幕降临,车厢灯灭了。我沿着车厢找人,走到最后一节货厢。门吱呀一声开了,黑暗中,有人迅速闪进来。
“别动!”他捂住我的嘴,把我按在车厢壁上。
我心跳如鼓,挣扎着想喊。黑暗中,他的气息近在咫尺:“别出声。转身出去,别回头。”
我僵硬点头。他松开手,胸膛的震动让我后背发麻。我低声问:“你受伤了?有血腥味,需要帮忙吗?”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出去,回车厢。”
我咬唇,快步离开。回到卧铺,心还在狂跳。他是谁?为什么有血腥味?
次日清晨,他回来了,换了身干净衣服,像没事人一样。他把早餐放桌上,依旧沉默。我小口吃着,偷偷观察。他神色如常,唯独眼神更深邃了些。
我鼓起勇气:“你叫什么?”
他愣了片刻:“贺铮。”
我点点头:“我叫简月清。”
他轻嗯一声,没多说。沉默片刻,他又道:“中午自己去餐车吃。晚饭我给你带。”
我看了一眼箱子,低声说:“箱子别丢了。”
他笑了一下:“放心,不会丢。”
我脸一红,低头吃完早餐。他收拾碗筷,动作利落,像在军营里练过千百次。
火车接近西宁,窗外雪化了,露出斑驳的黄土。我收拾好资料,走向餐车。人群拥挤,我吃得慢,回去时车厢乱成一团。
几个军人模样的人按着几个犯人,吵嚷声不断。一个女人尖叫:“凭什么抓我?坐车也犯法?”
贺铮站在走廊,逆光而立,声音冷硬:“拐卖妇女儿童,我盯你们很久了。带走!”
我愣在原地。那女人,竟是第一天跟我搭话的大姐。贺铮的目光扫过来,我心一紧,低头避开。
人群散去,他走近我:“吃得比平时快啊。”
我扣着手:“饭菜不好吃,没吃完。”
他笑了,低声吐槽:“还挺挑食。”
我脸一热,没接话。他背上包,提着箱子:“我有事提前下车。晚饭托乘务员给你买。”
我连忙摇头:“不用麻烦了。”
他语气坚定:“答应的事得做到。”
他转身离开,短发下的旧疤痕在阳光下若隐若现。我收回目光,心底泛起一丝莫名的失落。
西宁站到了。黄沙扑面,刮得脸颊生疼。我提着箱子,挤出车厢,拨通科研所的电话:“我是简月清,到了西宁。”
对方惊讶:“简同志来得早!我们没安排接站。你先找地方落脚,我尽快派人。”
我应下,在附近旅馆安顿好。次日中午,一辆老旧解放牌汽车停在旅馆外。我穿着白色衬衫,军绿色阔腿裤,站在门口等候。
他也愣住,眼神闪过一丝意外:“你在这?”
我点点头:“来科研所报到。你呢?”
他笑笑:“任务,路过。”
我们对视一眼,空气里多了丝微妙。他把包放进车里:“上车,我送你一段。”
我犹豫片刻,上了车。汽车颠簸,戈壁的风沙从窗缝钻进来。我握紧箱子,问:“你常跑这种任务?”
他目视前方:“习惯了。”
我没再问。车停在科研所门口,他帮我拿下箱子:“到了,自己小心。”
我道谢,看着他开车离去。背影洒脱,像戈壁上的一棵孤树。
科研所里,同事们热情迎接。陈燕一把抱住我:“月清,你可算来了!”
我笑笑:“不来,你们还不得骂我?”
她拍我肩:“赶紧干活!咱们的实验等你呢!”
我投入工作,翻阅资料,调试仪器。忙碌让我忘了心痛。晚上,我站在宿舍窗前,戈壁的星空辽阔无边。我深吸一口气,像在和过去告别。
与此同时,青岩军区。顾景舟站在我空荡的房间前,手中握着那枚梨花发卡。他敲门,无人应答。老板说:“那姑娘早走了,钥匙都还了。”
他愣住,心像被掏空。他翻遍房间,只找到那枚发卡。精致的梨花,像是她留下的最后痕迹。
他冲到火车站,站台空荡荡的。火车早已开走,带走了她,也带走了他未曾察觉的依赖。
他攥紧发卡,喃喃自语:“月清,你真的走了?”
我不知道他的追悔。那一刻,我在戈壁的星空下,第一次觉得,心里的枷锁彻底碎了。
4
我擦掉汗,笑笑:“总得干点实事。”
仪器屏幕上,数据跳动,像在诉说戈壁的秘密。我盯着数字,心跳加速。父母用生命换来的科研事业,如今由我接续。每次突破难关,我都觉得他们在天上看着我。
“月清,这组数据有问题!”同事杨青青喊道。
我走过去,皱眉检查。屏幕上,地质样本的异常值刺眼。我沉声说:“再测一次,换个样本。”
忙碌到深夜,实验终于有了突破。团队欢呼,我却站在窗前,望着星空。顾景舟的脸又浮现在脑海。我攥紧拳头,告诉自己:简月清,你已经放下了。
次日,科研所接到军区任务,要协助检测一批矿物样本。我带队前往青岩军区。车子颠簸,戈壁的风沙扑面。我裹紧围巾,心底却泛起一丝不安。
军区会议室,门推开,我愣住了。贺铮站在那里,军装笔挺,眼神冷峻。他也看到我,眉梢微挑:“简月清?”
我点点头,心跳有些乱:“你怎么在这?”
他笑笑:“任务。没想到又碰上你。”
会议开始,贺铮作为军方代表,讲解矿物样本的战略意义。他的声音沉稳,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低头记录,余光却忍不住瞥向他。短发下的疤痕若隐若现,像在诉说他的故事。
散会后,他走过来:“忙完了?一起吃个饭?”
我犹豫片刻,点头:“好。”
食堂里,饭菜简单。他夹了块红烧肉给我:“吃点好的,戈壁可不养人。”
我低头咬了一口,心底暖意流淌。他总在不经意间,给我一种被在乎的感觉。
“你的任务,危险吗?”我试探着问。
他笑得随意:“习惯了。倒是你,科研所的活儿不轻松吧?”
我点点头:“累,但值得。”
他看着我,眼神深了些:“你变了。比在火车上,多了点光。”
我一愣,心跳漏了一拍。他的话像风,吹乱了我的平静。
饭后,他送我回宿舍。戈壁的夜风凉得刺骨,他脱下军大衣披在我肩上:“别冻着。”
我低声说:“谢谢。”他的体温残留在衣服上,暖得让我有些慌乱。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脑海里全是他的身影。贺铮,像戈壁里的一棵孤树,坚韧又孤独。我摇摇头,强迫自己不去想。简月清,你来西北是为了事业,不是为了别的。
与此同时,青岩军区家属院。顾景舟坐在客厅,手中握着那枚梨花发卡。白雪柔端来茶,柔声问:“景舟,你怎么了?最近老走神。”
他摇头,眼神复杂:“没事。”
白雪柔坐下,握住他的手:“是不是因为月清?她走了,你心里不好受?”
顾景舟沉默片刻,低声说:“我欠她太多。”
白雪柔眼眶微红:“她那么好,成全了我们。你别自责了。”
他攥紧发卡,声音沙哑:“她为我做了那么多,我却没给过她什么。”
白雪柔轻叹:“你把她当妹妹,她明白的。”
顾景舟没说话,目光落在窗外。夜色深沉,像他心底的遗憾,越来越重。
几天后,我在实验场忙碌,贺铮突然出现。他递给我一瓶水:“歇会儿,脸色都白了。”
我接过水,笑笑:“你怎么又来了?”
他耸肩:“任务多,跑得勤。”
我喝了口水,试探问:“你老跑任务,不累?”
他笑得洒脱:“军人嘛,命硬。”
我看着他,忍不住问:“那道疤,怎么来的?”
他顿了顿,眼神暗了暗:“一次任务,擦着了。没事。”
我没再追问,心底却泛起一丝疼惜。他的世界,我触碰不到,却莫名想靠近。
实验场上的风沙更大了。我站在仪器前,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团队攻克了最后一道难关,欢呼声响彻戈壁。我笑了,第一次觉得,自己离父母的梦想那么近。
陈燕拍我肩:“月清,你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我摇头:“是大家一起努力。”
夜里,我站在宿舍外,戈壁的星空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我的心。顾景舟的影子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我对科研的热爱,和对自己的期许。
贺铮来了,背着作战包,眼神依旧冷峻:“明天我回部队了。”
我心一紧,点头:“一路平安。”
他看着我,笑了:“你这人,倔得像石头。可石头也有开花的时候。”
我愣住,心跳加速。他的话像火种,点燃了我心底的某处。
“简月清。”他突然叫我,声音低沉,“以后别把自己逼太紧。累了,就歇歇。”
我眼眶一热,强笑:“你也是。”
他没再说话,转身走向夜色。背影挺拔,像戈壁的孤树,扎根在风沙里。
几天后,顾景舟的信寄到科研所。他写道:“月清,我知道你不会回头。但我还是想说,对不起。这些年,我欠你一句真心的谢谢。”
我看着信,泪水滑落。不是为他,而是为那个痴情的自己。简月清,你终于走出来了。
我把信收好,抬头望天。星光璀璨,像在指引前路。戈壁的风吹过,带来新的希望。
贺铮的背影浮现在脑海。我笑了笑,或许,未来会有新的开始。但现在,我只想做最好的自己。